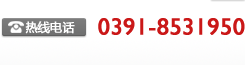自2009年新醫改以來,政府發文頻頻鼓勵社會辦醫舉辦非營利性醫院,但對于社會資本來說,舉辦非營利性醫院卻與其資本的逐利性所相左,致其動力不足。如何平衡社會資本的逐利性與公益性,我們需要思考現有的制度是否已經阻礙了醫療衛生行業的發展。未來,又將如何進行制度上的設計?本文將通過系列文章來為讀者進行詳細闡述。
醫院的發展歷史
醫院(Hospital)一詞來源于拉丁文“客人”,早期的醫院只是可以供人避難、休息,兼有招待意圖,后來逐漸演變成為收容和治療病人的專門機構。
我國是世界上早設置醫院的國家,周朝已開始初具雛形。《管子•入國篇》記載:“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在這九件事中,特別是慈幼、恤孤、養疾和問疾都與保健工作有著密切關系。公元前7世紀時,管仲輔助齊桓公執政,在國都建立了殘廢院,收容殘廢人,供給食宿,給予治療,這便是我國古代醫院的早期運營方式。《漢書》也有記載,在西漢年間,黃河一帶瘟疫流行,漢武帝劉徹就下令在各地設置醫治場所,配備醫生、藥物,免費為百姓治病。到了宋明時期,醫院組織日趨完備,當時政府辦的醫院叫做“安濟坊”,私人辦的稱“養濟院”、“壽安院”,以及慈善性質的“慈幼局”等,分門別類招收和治療病人。
歐洲早的醫院組織,則是基督教建于羅馬的醫療所,比我國晚了5個多世紀。法國的里昂和巴黎兩地分別于6世紀和8世紀建立醫院,英國倫敦則是7世紀才開始出現,而歐洲的第一家正式醫院是建于1204年的羅馬圣靈醫院(Hospital of the Holy Ghost)。18世紀資產階級大革命發生以后,醫院組織從宗教中脫離出來,開始獲得了新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類不但在經濟上實現了快速發展,在醫學科學和醫療技術方面日新月異,對醫療與健康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這些因素都促進了近代醫院向現代醫院的轉變,并且醫院的組織形態也隨之發生新的變化。
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研究
兩次世界大戰以后,戰爭給社會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和巨大浪費,引起了人們的深刻反思;此外,民族間的、地區間的、國家間的差別和矛盾繼續存在,并可能激化。在此大背景下,人們發現社會中的兩大部門(政府機構和私人營利機構,分別被稱為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已不能滿足社會經濟活動與公共需求的平衡需要。于是,社會組織形態開始蛹化,逐漸出現了第三部門——非營利性組織(也就是社會公益部門),并取得了空前發展。除了典型的慈善事業外,非營利組織的作用逐漸擴展到了教育、醫療、科研、福利、文化、藝術、環保、社會服務等多個領域。
一種社會經濟組織的存在有其內在的深刻原因,其存在必然反映了一些基本的經濟動機和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而這些機構組織以及允許其設立的法律的出現就是為了滿足這種需求。
伯頓•韋斯布羅德(Burton A. Weisbrod)指出,政府、市場和非營利部門是滿足個人對于公共物品需求的,存在相互替代性關系,非營利組織在捐贈人的資助和志愿者的無償勞動以及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存在,,同時,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可以在滿足公眾需求的背景下共同存在,是互補關系。而米亞(Meyer)認為政府提供的任何公共物品的數量和質量都是通過政治決策過程決定的,而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傾向于反映中位選民的需求,導致了公共物品對部分選民的過度供給,同時對另外一部分選民則供給不足,即出現政府失靈。對非營利組織產生原因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還包括漢斯曼(Hansmann)合約失靈理論(所謂“合約失靈”,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僅僅依據買賣雙方之間的合約(contract),難以防止商品生產者坑害消費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和萊斯特•薩拉蒙(Lester M. Salamon)“第三方管理”(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理論(非營利組織作為第三方出現,補充了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職能缺位)。
以上諸多理論的研究,表明非營利組織通過公平的競爭主體和公行的自律互律準則,能夠促進公益市場的透明化,提升公益組織的效率,增進社會的文明與和諧。
非營利組織涵蓋范圍之廣,主要特點體現在:一是不以營利為目的。非營利組織的建立不以利潤為目標,個人或單位提供資金創建非營利組織或擴大其運營規模,并不期望取得投資回報, 甚至不期望收回投資。非營利組織總體上是以宏觀的社會效益為目的,而非微觀的經濟效益,這一點上與私人企業有著本質區別。因此,區分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的基礎就是看其有無營利動機。二是“非分配”的約束條件。非營利組織的收人、利潤與財產不能分配給其員工、管理層或舉辦者,不能夠作損益計算和盈余分配,經營活動所獲得的收入和營利只能用于繼續再投入。三是政府給予免稅。鑒于非營利組織為公眾服務的性質, 國家免除其營業所得稅,有些還可免除其他地方稅,如財產稅等。
非營利性醫院的出現
費城賓夕法尼亞醫院(建立于1752年)、紐約醫院(1771年開業)以及馬薩諸塞總醫院(建立于1821年)作為美國早誕生的醫院,均是有希望得到醫療照顧的居民個人出于非營利的目的自愿籌建而成,醫院主要靠慈善捐贈來維持運營,向患者提供免費治療服務。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非營利性醫院開始診治付費病人,并通過它們所提供的服務和便利設施積極爭取這部分病人。截至今天,美國的非營利性醫院已經占到全部醫院數量的80%以上。
在全球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非營利性醫院幾乎在每個國家的衛生體系中都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不允許設立營利性醫院。
為什么非營利性機構在醫療衛生領域大量存在,而在其他大多數行業卻很罕見?例如,非營利性飯館、非營利性超市就非常罕見。主要在于以下兩種原因:
一是未被滿足的公共物品需求的提供者。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定條件下競爭行業在經濟學意義上是有效率的。經驗數據也表明,競爭促進增長。由此可知,在市場失靈的時候才需要政府部門,同理,在政府失靈時,人們反而又會需求非營利性機構。醫患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因素,導致醫療服務市場失靈,無法形成一個具有競爭性和營利性的醫療服務市場,因此這時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醫療服務,但是政府往往不能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于是作為補充,那些熱衷于社區服務的人士開始創建非營利性醫院。正是由于非營利性醫院沒有盈利的壓力,它們可以在趨于失靈的醫療服務市場生存。
在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 醫院先是作為慈善機構而出現,主要靠捐贈維持經營,承擔的主要任務也是向窮人提供服務。隨著醫療保險的出現,醫院才開始逐漸有了自己穩定的收入來源,而捐贈占醫院收入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到1996年,美國非營利性醫院中,捐贈收入平均只占到醫院收入的約3%。
二是對契約失靈的一種反應。肯尼斯•J•阿羅(Arrow)指出,非營利性機構盛行的原因在于鑒別保健質量的不確定性。漢斯曼(Hansmann)又進一步豐富了阿羅的觀點,他認為當購買者不能輕易覺察到所購買的產品數量或質量時,非營利性部門在一種特殊的契約失靈的情形中扮演了有用的角色。而醫療服務恰恰是患者無法進行準確判斷自己的需求,而且醫生極易誘導患者進行消費,因此很容易導致契約失靈的情形發生。非營利性機構的盈余不可分配,在客觀上其作假的激勵減弱,消費者對其可信度大幅提升,需求增加,進而這個市場趨向高效。同理,非營利性醫院向患者傳遞了“沒有作假動機”的信號,使得患者與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容易產生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場失靈。
從信息不對稱角度來說,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源于市場自我矯正市場失靈的一種機制,它的出現提高了市場效率。因此,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在醫療服務體系中占主體地位,并不是決策者刻意設計出來的,而是市場的選擇,是市場上“自愿交易”的結果。